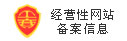曾子墨面試經(jīng)歷
時(shí)間:2015-11-26 09:11
來源:墨跡
曾子墨簡(jiǎn)介:

曾子墨,湖北武漢人,生于北京,鳳凰衛(wèi)視主持人。1991年進(jìn)入中國人民大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國際金融。一年后赴美留學(xué)。1996年畢業(yè)于美國達(dá)特茅斯大學(xué)(常春藤盟校),取得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學(xué)士學(xué)位。畢業(yè)后加盟國際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,先后在紐約、香港等地參與、完成大型企業(yè)收購及公司上市項(xiàng)目。2000年加盟鳳凰衛(wèi)視擔(dān)任節(jié)目主持人,先后主持過《股市直播室》、《財(cái)經(jīng)點(diǎn)對(duì)點(diǎn)》、《財(cái)經(jīng)今日談》、《世紀(jì)大講堂》和《鳳凰正點(diǎn)播報(bào)》?,F(xiàn)任鳳凰衛(wèi)視《社會(huì)能見度》、《我的中國心》和《經(jīng)濟(jì)制高點(diǎn)》主持人。 2010年6月底,因其“二奶無錯(cuò)論”被網(wǎng)絡(luò)熱炒。
曾子墨面試經(jīng)歷:
大三那年,我決定結(jié)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懶散生活,而要利用畢業(yè)前的最后一個(gè)暑假,讓自己的簡(jiǎn)歷錦上添花、盡善盡美。
然而10多年前,在投資銀行找工作難,找暑期工更難,找提供給本科生的暑期工則是難上加難。我始終相信,有的機(jī)會(huì)是從天而降的,有的機(jī)會(huì)則是需要親手創(chuàng)造的。于是,不論關(guān)系遠(yuǎn)近,也不論職位高低和資歷深淺,我那些屈指可數(shù)的在華爾街工作的朋友,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執(zhí)著的“騷擾”。終于,我把幾家主要投行的中國業(yè)務(wù)主管和人力資源主管姓甚名誰、電話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。結(jié)果,一切都在意料之中,發(fā)出去的求職信絕大部分石沉大海,在他們語音信箱里的留言,也都杳無音信。“做過暑期工的不過是鳳毛麟角,那么多沒有暑期工作經(jīng)驗(yàn)的人畢業(yè)后不也一樣進(jìn)了投資銀行?”我只能像阿Q一樣安慰著自己。
然而,奇跡真的就這么發(fā)生了。兩個(gè)月以后,柳暗花明:我竟然接到來自美林的電話,請(qǐng)我到紐約去面試。
關(guān)于面試的故事我聽說了許多,特別是初次面試,各種尷尬的場(chǎng)面時(shí)有出現(xiàn)。我的一個(gè)朋友,今天已經(jīng)是某著名投資基金的董事總經(jīng)理,當(dāng)年面試時(shí)就曾經(jīng)有過這樣一段對(duì)白:
招聘者問:“你為什么對(duì)Corporate Finance(公司融資)感興趣?”
朋友彬彬有禮地回答:“抱歉,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(投資銀行)。”
對(duì)方又問:“我是在問你,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?”
朋友很奇怪,心想怎么又問了一遍,于是更堅(jiān)定地回答:“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,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。”
“難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嗎?”
朋友頓時(shí)面紅耳赤,啞口無言,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癡。
Corporate Finance和M&A(收購兼并)一樣,都是投行業(yè)務(wù)的一部分,很多時(shí)候,人們會(huì)用Corporate Finance來泛指Investment Banking。通俗點(diǎn)說,他們那段對(duì)話好比就是:
“你為什么對(duì)做公安感興趣?”
“抱歉,我希望做的是警察。”
“我是在問你,為什么想做公安?”
“我不想做公安,我想做警察。”
我即將面對(duì)的是生平第一個(gè)面試,期待,興奮,可想而知。我前所未有地嚴(yán)陣以待,將大家的經(jīng)驗(yàn)之談悉數(shù)記在心中:千萬不能緊張,要落落大方,侃侃而談。為什么選擇達(dá)特茅斯,為什么愿意來到美林證券,答案一定要事先準(zhǔn)備。面試前幾天的《華爾街日?qǐng)?bào)》必須仔細(xì)閱讀,道瓊斯、納斯達(dá)克、恒生指數(shù)和主要的外匯匯率也都要熟記在心。握手的力度要適中,太輕了顯得不自信,太重了會(huì)招致反感。手中最好拿一個(gè)可以放筆記本的皮夾,這樣顯得比較職業(yè)。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,所以目光不能飄忽游移,只有進(jìn)行眼神的交流,才會(huì)顯得充滿信心。假如不敢直視對(duì)方的眼睛,那就盯著他的鼻梁,這樣既不會(huì)感到對(duì)方目光的咄咄逼人,而在對(duì)方看來,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觸。 套裝應(yīng)該是深色的,最好是黑色和深藍(lán)色,絲襪要隨身多備一雙,以防面試前突然脫絲。后來,我知道了投資銀行的確有些以貌取人,得體的服飾著裝可以在面試中加分不少。
做學(xué)生時(shí),我從來都是T恤牛仔,外加一個(gè)大大的Jansports雙肩背書包。為了讓自己脫胎換骨,向職業(yè)女性看齊,到了紐約,一下飛機(jī),我便直奔百貨商店Bloomingdale。
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頓中城,里面的套裝琳瑯滿目,每一款都漂亮得讓我愛不釋手。售貨小姐也熱情周到,伶牙俐齒地勸說我一件一件試穿,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試衣間時(shí)瞪大雙眼,對(duì)我贊不絕口。
試衣鏡里的自己果然煥然一新,看上去職業(yè)而干練。
“您是只選一套呢,還是多選幾套?”售貨小姐甜美的聲音讓我從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。我這才意識(shí)到,我居然忘記了看價(jià)格。
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實(shí)只屬于中檔,但是價(jià)格標(biāo)牌上那一連串的數(shù)字還是讓我望而生畏。畢竟,我只是一個(gè)依靠獎(jiǎng)學(xué)金生活的學(xué)生。我試穿的那幾套衣服加上消費(fèi)稅,最貴的有1000多美元,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。
“買?還是不買?”我激烈地進(jìn)行著思想斗爭(zhēng)。
“它們真的很適合你!”售貨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,努力作著最后的鼓動(dòng)。
這時(shí),旁邊的收銀臺(tái)突然來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顧客。看到她,我靈機(jī)一動(dòng),立刻拿出了 信用卡,態(tài)度之爽快,仿佛刷卡金額不是500美元,而是只有5美元。
售貨小姐笑容可掬地為我結(jié)帳、包裝。她大概并不清楚,24小時(shí)后,等眼前這個(gè)對(duì)職業(yè)化裝扮的自己甚為滿意的女孩參加完面試,就會(huì)原封不動(dòng)地把這套Ellen Tracy的西裝退還給她,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筆“巨額款項(xiàng)”。
第二天,穿著那套似乎專門為我定制、卻又并不屬于我的深藍(lán)色套裝,我鎮(zhèn)定自若、胸有成竹地走進(jìn)了美林的會(huì)議室。
面對(duì)來自香港的兩位銀行家,半個(gè)小時(shí)里,我學(xué)著美國人的方式,滔滔不絕地自我推銷,把自己說得像愛因斯坦一樣聰明,像老黃牛一樣勤奮,又像老鼠愛大米那樣深深地?zé)釔弁顿Y銀行。
握手告別時(shí),在他們的臉上,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:這個(gè)女孩,天生就屬于投資銀行。
在美林度過的那個(gè)夏天,我并沒有學(xué)會(huì)太多的金融知識(shí)或操作技能,但是,它卻為我打開一扇窗戶,讓我欣賞到投資銀行的美麗風(fēng)景,并且從此立下志愿:我要真正成為華爾街的一分子。
于是,四年級(jí)一開學(xué),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輪又一輪看不到盡頭的面試旋渦里。和每一位忙著找工作的96級(jí)學(xué)生一樣,盡管11月的達(dá)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,我卻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氣里穿著西裝短裙和薄薄的絲襪,披著黑色長(zhǎng)大衣,腳蹬高跟鞋,在漢諾威旅館和教室宿舍間來來回回,奔走穿梭。
漢諾威旅館是投資銀行來學(xué)校進(jìn)行前兩輪面試的地點(diǎn)。那陣子,那里天天爆滿,每一層的走廊里都擠滿了西裝革履的學(xué)生,或站或坐,不安地等待著房間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。
投資銀行的面試看上去層層關(guān)卡、危機(jī)四伏,但涉及的問題卻多半是“老三樣”。
“講述一下你自己的經(jīng)歷。”
“朋友們會(huì)用哪幾個(gè)詞來形容你?”
“為什么我們應(yīng)該錄用你?”
無論提問方式如何變化,我總是喜歡亮出我的“自我表揚(yáng)一二三四”,以不變應(yīng)萬變:
我聰明好學(xué),能夠很快適應(yīng)新的環(huán)境;
我擅長(zhǎng)數(shù)字和數(shù)學(xué),諸多相關(guān)科目的A+成績(jī)就是最好的證明;
我勤奮刻苦,一周工作八九十個(gè)小時(shí)不在話下;
我善于合作,是個(gè)很好的團(tuán)隊(duì)工作者。
面試的時(shí)間再長(zhǎng),也長(zhǎng)不過40分鐘。人人都怕刁鉆古怪的問題,我也一樣。于是,一旦遇到“正中下懷”的提問,我就伺機(jī)大講特講,口若懸河,再不易被察覺地“延伸”到我悉心準(zhǔn)備的其他答案,直至面試接近尾聲,對(duì)方不再有時(shí)間也不再有機(jī)會(huì)來為難我。
那年第一次面試,是和第一波士頓(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)的一位副總裁。 第一波士頓為我面試的那位副總裁看上去只有30歲出頭。那天,他大概已經(jīng)從早上8點(diǎn)到下午4點(diǎn),端坐在酒店房間里那個(gè)并不太舒服的沙發(fā)上,馬不停蹄地見過了十幾名學(xué)生。輪到我走進(jìn)去時(shí),他早已滿臉疲憊,連握手時(shí)的笑容都像擠牙膏一樣勉強(qiáng)。
“Ok,tell me about yourself.”不出所料,他提出的第一個(gè)問題中規(guī)中矩。 我微微一笑,神采奕奕地講述了自己的經(jīng)歷,又有條不紊地將我的“一二三四”暗藏其中。副總裁斜靠在沙發(fā)上,邊聽邊點(diǎn)頭。第一個(gè)問題,我順利過關(guān)了。“你怎么證明你善于團(tuán)隊(duì)合作呢?”我故意擺出一副沉思的樣子,其實(shí),我的內(nèi)心是在暗自得意。誰讓我又碰到了一個(gè)押中的題目呢?不過,我不想讓他看出我是有備而來。略微停頓了幾秒,我按照設(shè)計(jì)好的思路,開始繪聲繪色地講述我的“軍旅生涯”。
在北京念書時(shí),我曾經(jīng)先后兩次到38軍軍訓(xùn)。這在中國算不上是出眾的經(jīng)歷,但到了美國,卻是傲人的資本。40多天的軍旅生活,除了難耐的饑餓和沉積著黃沙的渾水,還留下了什么呢?沒想到的是,4年以后,身在異國他鄉(xiāng),我卻突然發(fā)現(xiàn)曾經(jīng)讓我叫苦連天飽受摧殘的軍訓(xùn)竟然變成了面試時(shí)的制勝法寶。
面對(duì)第一波士頓的那位副總裁,短暫軍旅生活中被饑餓和惡劣的衛(wèi)生條件所掩蓋的另一面,居然都在我腦海里重新鮮活起來。我活靈活現(xiàn)地回憶起在軍隊(duì)的大集體里,在團(tuán)隊(duì)成員的相互幫助下,我們?nèi)绾卧谀嗌郴祀s的戰(zhàn)壕里匍匐前進(jìn),如何在烈日當(dāng)空時(shí)俯臥打靶,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輪流站崗值班,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時(shí)被哨聲驚醒,迷迷糊糊地打背包,連滾帶爬地緊急集合,再像殘兵敗將一般,翻山越嶺“急行軍”……
聽著聽著,副總裁的身體坐得越來越直,原本無精打彩的眼睛也變得炯炯有神。那時(shí)候,我就已經(jīng)知道了,當(dāng)我走出那個(gè)房間后,即便他記不住我的名字,也一定會(huì)記住有個(gè)中國女孩,她曾經(jīng)在中國軍隊(duì)里摸爬滾打。我還確信,只要被他記住了,百里挑一的第二輪面試我就一定榜上有名。
果然,他一連說了三個(gè)“great”,才又接著問:“聽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,你有什么缺點(diǎn)嗎?”
“英語畢竟不是我的母語,所以和美國同學(xué)相比,我想,這是我最大的弱點(diǎn)。”我坦然應(yīng)對(duì),并沒有遮遮掩掩,因?yàn)槿绻芑秉c(diǎn)為優(yōu)點(diǎn),化不利為有利,遠(yuǎn)比一味陳述自己的優(yōu)秀更有說服力。
“但是,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。剛來美國時(shí),我每天除了上課和打工,還要至少花一兩個(gè)小時(shí)守在電視機(jī)前看新聞,為的就是練習(xí)英語。另外,雖然我在英文寫作課上的成績(jī)是A和A-,但我并沒有就此停滯不前……”
因?yàn)閾碛薪咏?.9的學(xué)積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經(jīng)歷,我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幾乎所有大型投資銀行的初次面試;然后,憑借充分的準(zhǔn)備和逐漸嫻熟起來的技巧,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輪面試中過五關(guān)斬六將,一次次地飛往紐約,接受最后的考驗(yàn)。
進(jìn)入第二輪面試,常常是應(yīng)試者同時(shí)面對(duì)兩個(gè)人提問,半小時(shí)后,再邁入另外一個(gè)房間,接受同一家公司另兩位銀行家的評(píng)判。
兩位考官,常常一個(gè)扮“好人”,一個(gè)扮“惡人”。與摩根斯坦利進(jìn)行第二輪面試時(shí),我就曾經(jīng)成功地把“惡人”感化成了“好人”。那天上午9點(diǎn),我準(zhǔn)時(shí)走進(jìn)約好的房間,兩位男士早已經(jīng)在那里等候。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來,熱情地說:“子墨,你好。我是Mike,M&A的董事。這位是我的同事,Merchant Banking的經(jīng)理,Rob。”一見Rob好似陰天的表情,我就知道,他一定是那個(gè)“惡人”。“為什么對(duì)投資銀行感興趣?是因?yàn)殄X,還是因?yàn)橄矚g接受挑?”
好人Mike拋出的第一個(gè)問題如同一份押中了50%的試卷,前一半在復(fù)習(xí)范圍之內(nèi),后一半?yún)s只好臨場(chǎng)發(fā)揮。比臨場(chǎng)發(fā)揮還折磨人的是,這個(gè)問題讓人左右為難:雖然無論對(duì)本科畢業(yè)生還是MBA,投行的起薪確實(shí)高于平均水平,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錢,你會(huì)被看作“貪婪”,如果答案是挑戰(zhàn),又會(huì)被視為“虛偽”。
我該怎么辦?此情此景,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輕,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:“投資銀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個(gè)很好的學(xué)習(xí)機(jī)會(huì)。首先,我可以學(xué)習(xí)到很多技能,比如,評(píng)估資產(chǎn)價(jià)值,幫助企業(yè)融資,協(xié)助公司通過收購兼并來提高核心 競(jìng)爭(zhēng)力和把股東價(jià)值最大化,還有談判以及如何與律師、會(huì)計(jì)師一起創(chuàng)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構(gòu);其次,投資銀行集中了許多聰明能干經(jīng)驗(yàn)豐富的專業(yè)人士,與他們一起工作,我一定會(huì)有收獲;第三,美國經(jīng)濟(jì)高度發(fā)達(dá),資本市場(chǎng)功不可沒,我希望通過投資銀行的工作,近距離地觀察資本市場(chǎng)如何推動(dòng)資源的有效配置,又如何推動(dòng)經(jīng)濟(jì)的發(fā)展。另外,我對(duì)投行感興趣是因?yàn)槲曳浅_m合投行的工作……”
設(shè)計(jì)這樣的答案,“首先”是為了告訴對(duì)方,我了解投行的業(yè)務(wù),“其次”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,當(dāng)然主要是為了讓他們倆人高興,“第三”是表明我還有宏觀的視野,最后,之所以又把“自我表揚(yáng)一二三四”加了進(jìn)去,哪怕有些答非所問,是因?yàn)槲也荒芊艞壢魏我粋€(gè)詮釋自己的機(jī)會(huì)。而且,我必須為自己贏得時(shí)間,必須在滾瓜爛熟地背誦“臺(tái)詞”時(shí),騰出一半大腦,認(rèn)真地思考“錢和挑戰(zhàn)”,我到底該如何應(yīng)對(duì)。
“做投資銀行的確是很好的學(xué)習(xí)過程,但是錢呢?錢重要嗎?”“惡人”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戲,將了我一軍。
“不能否認(rèn),投行的薪酬是有誘惑力的,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時(shí)來計(jì)算,分析員每小時(shí)的薪酬又能比在 麥當(dāng)勞打工高多少呢?人應(yīng)該有長(zhǎng)遠(yuǎn)的目光,作為職業(yè)生涯中的第一個(gè)工作,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,而是你學(xué)到了什么,能讓你終生受益。”
短短的幾句話,我眼看著Rob的表情陰轉(zhuǎn)多云,又多云轉(zhuǎn)晴。我知道,我的左右逢源又幫我逃過了一劫。
在一家投行的前兩輪面試中,通常要接受五六個(gè)人的“拷問”,到紐約參加最后一輪面試,則要在一天之內(nèi)至少見8個(gè)人。這么多輪面試成百上千的問題中,“錢”的問題并不算刁鉆,Rob也不算最惡的“惡人”。
參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輪面試時(shí),一位分析員剛走進(jìn)會(huì)議室,樣子就讓我頗為意外:他的襯衣袖子高高地挽起,領(lǐng)帶歪斜著掛在胸前,雙眼還布滿了通紅的血絲。面無表情地與我握手寒暄后,他不動(dòng)聲色地發(fā)問了:“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,薪水有兩種支付方式:一年12000美元,一次性全部給你;同樣一年12000美元,按月支付,每月1000美元。你會(huì)怎么選擇?”
我心里“嘭”地一跳,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??!
我囑咐自己千萬別慌,剛要迅速回答,卻又突然意識(shí)到,如果簡(jiǎn)單地說選擇第一種,答案太過絕對(duì)了。
我想,我不如搬出課本里的名詞:“這取決于現(xiàn)在的實(shí)際利率。如果實(shí)際利率是正數(shù),我選擇第一種;如果是負(fù)數(shù),我選擇第二種;如果是零,兩者一樣。同時(shí),我還會(huì)考慮機(jī)會(huì)成本,即便實(shí)際利率是負(fù)數(shù),假如有好的投資機(jī)會(huì)能帶來更多的回報(bào),我還是會(huì)選擇第一種。”說完這一長(zhǎng)串的答案,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,因?yàn)槲抑阑卮疬@類問題時(shí),相對(duì)于答案本身,思考的過程更被看重。“一般人都說選擇第一種,你還不錯(cuò),考慮得很周全!”淡淡的一句點(diǎn)評(píng)后,他并沒有就此罷休,“那實(shí)際利率又是什么呢?”“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。”幸好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基礎(chǔ)知識(shí)還沒有完全荒廢,我在心里慶幸。“現(xiàn)在的聯(lián)儲(chǔ)基金利率是多少?通貨膨脹率在什么水平?”這一次,我真的被問住了!我實(shí)在想不通,我與他素昧平生,他何苦這么咄咄逼人呢?
準(zhǔn)備面試時(shí),我就告訴自己要秉承一個(gè)原則:不懂的千萬不能裝懂,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編亂造。于是,我老老實(shí)實(shí)地回答:“對(duì)不起,我不知道,不過如果需要,我回去查清楚后,馬上打電話告訴你。”
后來,我的確聽說過一個(gè)中國女孩為了表現(xiàn)自己與眾不同,告訴面試她的美國人,說她的最愛是開 賽車。乖巧的東方瓷娃娃卻熱愛西方式的瘋狂和刺激,這讓從小就不說謊的美國人信以為真,神魂顛倒。然而,公司里的中國同事卻一語道破天機(jī),斬釘截鐵地說這個(gè)女孩是在杜撰。結(jié)果可想而知,空歡喜一場(chǎng)的美國人發(fā)現(xiàn),乖巧的“瓷娃娃”居然連駕照都沒有,于是高呼上當(dāng)受騙,而那個(gè)中國女孩,自然也無緣那份工作。
那位分析員不依不饒又提出一個(gè)通常只有咨詢公司才會(huì)問的智力測(cè)驗(yàn):“9個(gè)硬幣,有一個(gè)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樣,你用兩只手,最多幾次可以找出這枚特殊的硬幣?”
“三次。”我不服輸?shù)仫w快回答。
“還是9枚硬幣,改變其中的一個(gè)條件,兩次就可以找出這枚特殊的硬幣,這個(gè)條件應(yīng)該怎么修改?”
“告訴我這枚特殊的硬幣比其他的硬幣重還是輕。”
當(dāng)我再一次以飛快的速度給出了正確答案,他終于低聲說了句“Good”,然后問,“你現(xiàn)在有沒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?一共有幾個(gè)?是哪些公司?”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,他的表情終于不再橫眉冷對(duì),提的問題也終于走上了正軌。
據(jù)說在我的評(píng)定書上,他填寫的意見是:不惜代價(jià),一定要雇傭!

 粵公網(wǎng)安備 44190002001278
粵公網(wǎng)安備 44190002001278